编者按:燕永同学回忆录第五章《我的大学》,以细腻、生动的笔调,描绘出1978——1982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,我校莘莘学子发愤学习、善待生活的多彩场景和同学友爱、师生交融的动人画面,展现了七八十年代大学生"团结、朴实、勤奋、进取"的高风峻节和勤勉风采,从中可窥见他们充满朝气、笃行不怠、自强不息,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足迹。朴素的字里行间,反映了南京林业大学"诚朴雄伟、树木树人"的办学特点和精神风貌,颂扬了学校领导和老师爱生如子、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。读后感人至深、催人奋进,对校友们今后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。
鉴于篇幅较长,我们将分八次进行转载。因时间久远、内容浩繁,文中可能存在一些记忆、理解的偏差,同学们发现后,可以和校友办或作者联系,以便及时修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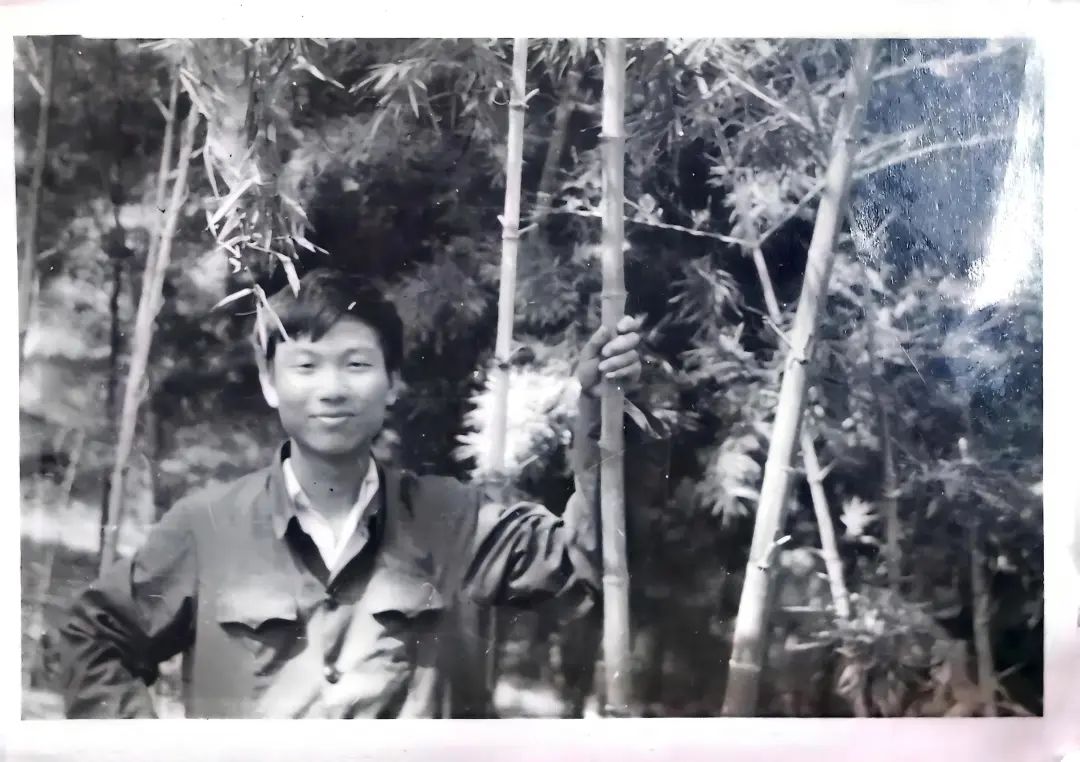
农民的地里是不能去了,我们几个也老实了一段时间。一个星期天上午,我正在宿舍看书,朱自德过来说:"别看了,休息一下。走,去喊卫国到洪启那看看有没有好吃的。"我们三个便来到郭洪启的房间,可屋里空空如也,什么吃的都没有,正在大家为没东西解馋发愁的时候,朱自德看到墙边的捕虫网(实习《森林昆虫学》时,捕捉昆虫、制作标本用的),眼睛一亮,开口道:"树木园里经常有松鼠、野鸡、刺猬、兔子出没,以前我在家抓过野味,俺们带上网子,说不定能抓只野鸡回来饱饱口福,中不中?"一听这话,大家顿时来了精神,说干就干(当时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,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直到1988年11月才出台),我们四人马不停蹄地来到树木园,朱自德摘了一些红艳艳的山莓果(野草莓),撒在一片草地上,然后让大家躲藏在旁边灌木后面耐心等待。一晃过去两个多小时,除有两只兔子一窜而过外,也没见到其他动物的影子,就在大家焦躁失望准备离开时,忽然从树林里飞来三只五彩斑斓的野鸡,落在撒了红果子的草丛中,朱自德眼疾手快,对准前面一只大的网了下去,谁知由于他心里紧张,仅罩着半个身子,这只足有三斤多重的野鸡扑腾几下挣脱出来,就在它起身欲飞之际,朱自德再次挥网,把它死死罩住,大家见状一片欢呼。带着"战利品"回到郭洪启的房间,郭洪启赶紧杀鸡拔毛,清洗干净后加点食盐在脸盆里炖煮,不一会盆里香气四溢,令人垂涎欲滴。大家拿碗举箸,大口朵颐着原汁原味、鲜美可口的野鸡汤(肉),啧啧咂舌、酣畅淋漓。

学校书本、住宿、看病就医等一律免费;寒暑假回家生病治疗,凭医院发票开学后在学校全额报销;生活费(助学金)则依据家庭收入情况评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级,入学时甲等14.7元、乙等8元、丙等5元、丁等3元,家里收入高的或带薪上学者(入学前是国家干部职工、工龄满五年,上学期间工资原单位照发)则一分没有。一年多后进行上调,甲等17.8元、乙等11元、丙等8元、丁等5元,对部分家庭困难、享受甲等的同学每月还有4元补助,加起来有21.8元,不仅够在学校的生活开支,还可以节约一部分支援家里。一到月末,生活委员就会把补助的生活费以饭菜票的形式发给大家,同时还发些布票、糖票、香烟券、工业券等,农村来的同学大都能评上甲等,足够在校吃饭和生活开支。我因父母工作被评为乙等,开始每月家里寄15元补贴,补助增加后每月寄10元,加在一起21元(当时刚参加工作的工人每月工资仅18元),虽不十分富余,倒也衣食无忧。 1979年中美建交后,校园内掀起一股学外语的热潮,我向父母要了40元钱买了一台熊猫牌单卡录音机,期望对学习英语有所帮助,而当时邓丽君、张帝、苏小明、关牧村等的歌曲风靡一时,一些同学和我都弄些磁带放音乐、听歌曲,英语也被搁置一边,没有什么大的进步。母亲后来为了方便我的学习和生活,又把她的手表给了我,当时学校有录音机和手表的人非常少。父母"望子成龙",节衣缩食、尽其所能地支持和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,使我深深感受到了什么是"可怜天下父母心"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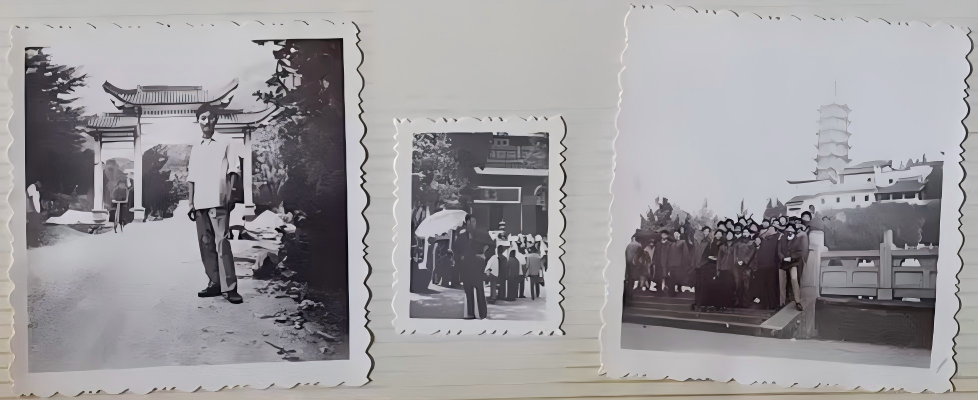
由于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,家庭经济条件有限,所以大家的生活都比较清贫,好在同学们大都是吃惯了苦过来的,况且学校的生活比当时的农村还好许多,所以都能坦然面对,毫无怨言。大家平时生活也非常俭朴节约,除一两个年纪较大的同学有时抽点香烟外,其他同学都是烟酒不沾。衣服春秋两季大都穿着从家里带来的蓝、黑、灰色粗布中山装,谁有件的确良或的卡衣服其他同学都羡慕不已。有的衣服少,只能晚上洗了晾干后第二天继续穿。我有一件蓝色的铁路制服,邱辉有一件绿军装,我俩时常换着穿,显得衣服多点。有位来自贫困山区的同学,父母一个长期患病、一个身有残疾,三个弟妹尚未成年,高中一毕业就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,但他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,带着东借西凑的20元钱到县城高考复习班学习,平时借宿在亲戚家的杂物间里,没有饭吃就到街上去乞讨,考上我校后一日三餐以咸菜、青菜佐饭,每天伙食费不超过两毛钱,把省出的菜票卖给不够的同学,再按月寄给家里。不少同学夏天洗澡,用自来水冲一冲,冬天则提一瓶热水、拿个脸盆在厕所内擦洗一下,以省掉五分钱的澡票(也是部分同学的一顿菜金);一些同学为省一毛多钱公交车票,到市里新街口、鼓楼等地都来回步行十几公里。我也常从学校树木园穿过南京市苗圃(当时学校只有一个常年敞开的南门,校区也没有围墙,许多小路直通校外),步行到南京火车站邮电局拿包裹、取汇款、打电话。大学四年,极少有人在外面吃饭,感觉出去办事一时回不来,临走时便让同学帮忙打好饭菜,等回来再吃。寒暑假有的同学也不回家,一是节省路费;二是可以在学校勤工俭学,如刻蜡纸、当保安、搬运货物、到苗圃打零工等,挣点辛苦钱,以弥补经济不足,和现在有些大学生住宾馆、下饭店,攀比名牌、到处旅游相比,真是天壤之别。校内中国林科院林化所斜对面、学校生活服务区有个商店,许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,还有医院、理发室、浴池、中小学、幼儿园、粮站等,教职工和学生生活都比较方便。食堂的伙食也是物美价廉,早上稀饭、馒头和咸菜;中午、晚上以大米饭为主,有时是花卷、包子。菜品花样有十几种,青菜五分钱一份,鱼肉等荤菜一两毛一份,其中卤猪肺、叉烧肉、炒里脊、狮子头、盐水鸭等非常美味,也是我不常吃但最爱吃的几个菜。毕业后,无论我自己在家反复做还是到各大小饭店去点,再也品尝不到学校食堂的那种味道了。如遇生病,凭校医院证明可以买到面条之类的病号饭。后来为满足部分师生和职工生病、来客人和民族习惯的需求,学校在大食堂东边开了个小食堂(校内和周边无一家饭店或小吃铺),我生病或不舒服时,偶尔去花二毛五下碗肉丝鸡蛋面或四毛钱来个小炒,也算是下了趟"馆子"。晚上偶有挑着馄饨担子的小贩在宿舍楼下叫卖,个别同学下楼买上一碗,惹得其他同学很是眼馋。端午节、中秋节、国庆节、"五四"青年节等食堂不仅菜的花色品种有所增加,还有粽子、月饼、糕点和水饺等,每个同学另发一张加餐券,改善生活,欢度节日。当时学校的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好,食堂师傅为同学们的一日三餐竭心尽力,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。

在我上大学期间,先后有老家好友杨培善、陈福龙和已定居香港的堂姐夫陈国光来学校看望过我,亲友异乡相会让我非常高兴,白天有空就陪他们一块到市区或学校周边去游玩,中午回学校就餐,晚上则一起挤睡在我的单人床上。特别是姐夫陈国光见我经济不太宽裕,回香港后寄来30元港币,我和邱辉一道来到位于鼓楼的友谊商店(专供兑换外币或用外币购买商品),兑换了100多元人民币并获得几张工业券的奖励。这笔钱对于我来说如雪中送炭一般,改善了近半年的生活。另外还和在南京邮电学院上学的颍上老乡高柏红、在南京铁路运输学校的女老乡朱化侠以及本校老乡李家东(曾任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)、李炳凯(曾任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教授)、杨文华(曾任宿州市林业局总工程师)、甄茂清(曾任合肥市园林学校副校长)等常有来往。记得有一天,家境并不富裕的杨文华,看我脚上穿的皮鞋已经破旧,便跑回宿舍,把自己仅有的一双稍好些的皮鞋洗净擦好拿给我。因鞋子太大,几天后我便送还给他,但这份老乡情谊感人肺腑,让我至今铭记在心。那时交通比较落后,回家、返校都要几经转车,花费不少时间。为方便学生购票,一到寒暑假,南京火车站的工作人员都会来到学校设立窗口、送票上门,我们凭学生证火车票价格减半。我有时走芜湖过长江轮渡换乘到淮南,然后再坐汽车到颍上;有时和朱自德、万永辉(他们去信阳罗山)一道到蚌埠换车去阜阳。火车和汽车很少能坐到位子,都站在拥挤不堪的车厢内,每走十几公里就有一个站,肩挑手提农副产品和家禽水产的农民便会一拥而入,不仅腥臭难闻,连站脚的地方都难寻。火车和汽车时走时停,车速平均每小时不到50公里,还要转乘几次,所以每次回家或返校,300多公里的距离,不论走哪条线路,,都至少要两三天的时间。旅途因经济拮据,从没住过宾馆或旅社,都是在汽车站、火车站过夜;饿了就啃几口出发前在学校买的馒头或面包,有时一天吃不到东西、喝不到开水,颠沛劳累,甚是辛苦。现在高铁、高速四通八达,颍上到南京高铁不到两小时,高速也只需三个多小时,真是沧海桑田,变化巨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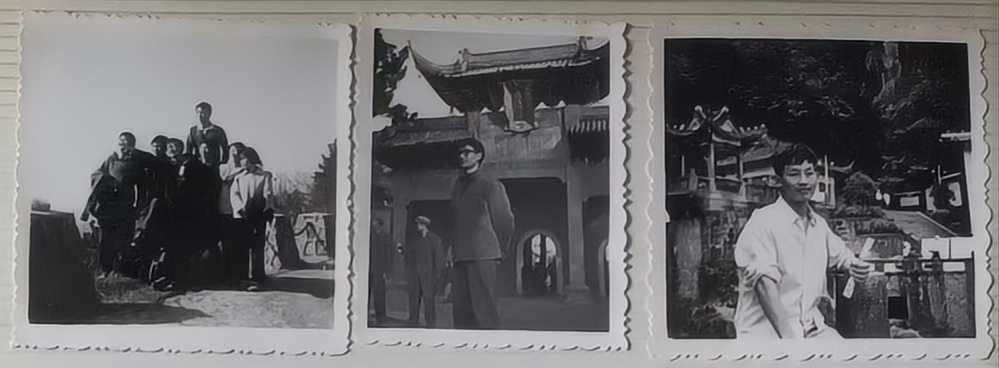
附:作者简介
本文选自燕永回忆录《烟雨平生》。燕永,安徽颍上人,1962年10月生,1978年8月高一考入南京林产工业学院(现南京林业大学)。1982年8月毕业,先后在广德县林业局、阜阳行署林业局、阜南县张庄乡人民政府(挂职)、安徽省乡镇企业局、安徽省中小企业局、安徽省经委、安徽省经信委(厅)工作。曾任《阜阳地区林业志》编纂办公室副主任、安徽省乡镇企业局主任科员、《安徽乡镇企业》杂志社副社长兼主编、安徽省中小企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副主任、安徽省中小企业培训中心总工程师、安徽省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、安徽省煤炭安全考试中心主任等职,2023年11月退休。
欢迎各位校友积极投稿!
投稿邮箱:nlxyh@njfu.edu.cn
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毕业院系、专业名称、届次(年级班)及工作单位(可选)、通信地址及电话邮箱等以便联系。
